想象一下,你正置身于湖畔的一座古旧宅邸之中。时间是夜里,外面暴雨肆虐,狂风绕着灰色的石墙嘶吼。房子下面的一间阴森的地窖里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玛德琳小姐的尸体。同你一起待在房间里的是她的哥哥,正在用疯狂的目光望着你。想象一下吧……你这是在鄂榭府上。
翻到另一页,可以见到一只黑猫被人勒住脖子吊在树上。再翻一页,你就会听到一次美妙绝伦的假面舞会上响起的音乐声,看见一千个人在唱歌、跳舞。你现在是在普洛斯佩罗亲王的城堡中。城堡里面灯火通明、生气勃勃,人人纵情狂欢;但是在城墙外面,逡巡着那可怕的载面具的红死魔……
这些故事将会带你进入一个阴暗的幻想世界,一个充满了恐怖、梦幻与疯狂的世界。
不要一个人读它们!
【编辑推荐】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是一套适合小学到大学的分级读物,是一套精心制作的阅读材料,帮助学生从培养兴趣开始,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把学生引入英语的殿堂。让学生逐渐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体验,使英语学习成为一种享受。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选材科学:所有题材均出自世界优秀文学名著或原创佳品;英汉对照:在当页提供汉语翻译,便于学生及时印证阅读效果;注释语言点:当页提供语言点、生词注释,方便学生抓住核心词汇;配有练习:方便学生检验阅读效果,把握语言点;单册包装、分级盒装和全套盒装,为自用及馈赠亲友提供多种选择。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至今已热卖50000000册。

【作者简介】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在短暂而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中,他曾供职于几家报社,并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和诗歌。也许最令他声名远播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
【目录】
鄂榭府崩溃记
黑猫
红死魔假面舞会
威廉·威尔逊
泄密的心
【书摘与插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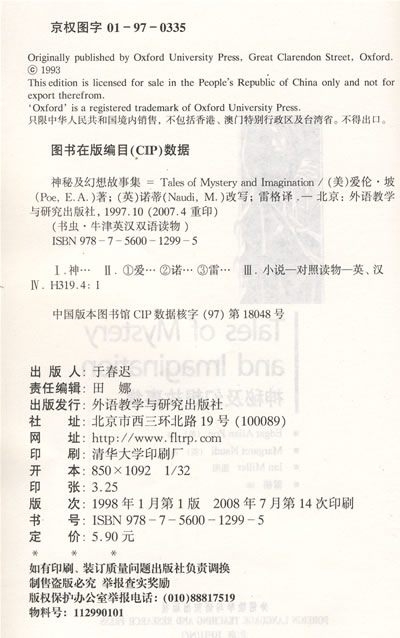
【免费在线读】
鄂榭府崩溃记
这是秋日里灰蒙蒙的一天,空中积满了大团大团的乌云。整整一天,我骑着马从平淡、乏味的乡野间驰过;不过,到天色开始变得昏暝的时候,我终于望见了此行的目的地。
在我眼前,兀然立着鄂榭府。一看见它——不知何故——一种阴悒至极的怪异感觉便降临在我身上,像一张毯子一样罩住了我。我抬头仰望这座有着高大的石墙和狭小的窗户的古旧府第,又环顾四周稀疏的枯草和垂死的老树,这时,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心。我觉得奇寒彻骨,浑身乏力,怎么也想不起一件乐事来驱散心头的阴悒。
我真奇怪,为什么鄂榭府会令我感觉如此之差?我百思不得其解。
紧挨着宅子有一个湖,我骑马来到湖边停住。也许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宅子就不显得那样黯淡、那样阴悒了。我低头朝幽暗、凝止的湖水望去,在倒影中再一次看见了房子上面空荡的、眼睛似的窗户,以及四周那些垂死的树。阴悒的感觉愈发强烈起来。
我将在这座府邸里盘桓几个星期。府邸的主人罗德里克·鄂榭,是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好友,我已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可是最近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一封透着悲哀与恐怖的信。他在信中说他患了病,身体和精神都不正常,还说他急切地要见我。找是他唯一的朋友,只有我能够帮助他摆脱疾病的折磨。
虽说我们年少的时候是挚友,但我对他了解得非常少。他极少谈及他自己,不过我知道他来自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世家,而他是这个世家最后一位活在人间的男性。我还知道,在鄂榭家族史上还从未有过子息繁盛的时候,于是,数百年来,家族的姓氏连同家族的宅第均是由父及子由子及孙一脉单传。
我站在湖边,心头阴悒的感觉一刻强似一刻。我同样清楚,这阴悒之情的下面暗伏着恐惧,而恐惧又以古怪的方式作用于我的头脑。我开始猜测这阴悒并不在我头脑中,而是某种真实的东西。它宛如一团神秘的云气,似乎是从幽暗的湖水、垂死的树和宅子破旧的墙垣中间径直升腾而起的。那是团沉重的铅云,饱含着疾病与恐怖。
我告诉自己这是个梦,又更加仔细地打量眼前的这栋建筑。的确,它已经非常破旧了,我注意到每一块石头上都有裂隙和孔洞。但是建筑本身又没有真正的残损,它一块石头也不缺。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道非常细小的裂缝,它从房子的顶部开始出现,然后一路向下延伸,直插入幽暗的湖水之中。
我来到宅子的正面。一个仆人牵走了我的坐骑,我跨进了大厅。另一个仆人默默地领着我上了楼。墙壁上挂着许多幅怪异、晦暗的画,让我十分紧张。我记得当年我还是个孩子、来这座府第里做客时就见过这些画,但是这次来访,它们给我的感觉却是前所未有的。
在楼梯上我们遇见了家庭医生,他脸上现出一副古怪的神情,这神情我很不喜欢。我急忙走了上去;终于,仆人打开门,引我走进了书房。
房间又大又长,窗户又高又窄,只能容许一点点天光射入,屋子的所有角落以及一件件深色的家具四周都是阴影。屋里摆放着好多书籍和几把吉他,但是毫无生气,毫无快乐可言。空气中满是浓重的阴悒氛围。
鄂榭一看见我,便起身热情洋溢地表示欢迎。我起初还以为他这只不过是做出来的殷勤态度,可是待我朝他脸上望去,才知道他见到我是真心欢喜。我们坐了下来,但他一开始并未开口讲话;有几分钟我就这样看着他,心里既吃惊又害怕。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他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的脸颊还是那样苍白、瘦削,眼睛还是那样大而清澈,嘴唇还是那样薄,头发还是那样柔软。但是现在,他的皮肤变得太惨白,眼睛变得太大太亮;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他把我吓坏了。还有他那一头乱糟糟的长发,好似幽灵般的愁云一样缭绕在他脑袋上。
我发现我的朋友极度神经质,情绪变化无常。有时他长篇大论地讲话,而后就会突然问变得沉默寡言,几个小时一语不发。还有的时候他觉得想问题特别困难,于是他说话的声音就变得粗重、迟缓,好像是一个饮酒过量的人发出来的。
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何急于见到我,以及他如何希望现在有我相陪伴,他的情况会好转些。他解释道,他得的是一种怪病,这种病已经在他的家族中肆虐好久了。这种神经过敏症搞得他对一切事物都比其他人敏感得多。他只能吃那些几乎完全寡淡无味的食物,只能万分小心地挑选衣物,因为大多数面料都会伤害他的皮肤。他不能忍受屋里摆放花卉,因为花卉的香气对他来说太浓烈了。光线会剌伤他的眼睛,大部分声音会剌伤他的耳朵——只有柔和的吉他弹奏声他还能接受。
最糟糕的是,他成了自己的恐惧的囚徒。“我要死了,”他常常说,“死于这种恐惧。我并不害怕危险。令我丧胆的是恐惧本身。此刻我在同恐惧搏斗,但迟早我会丧失这奋力搏斗的能力。”
在与鄂榭的长谈中,我对他的怪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坚信这个病症来自鄂榭府本身。他已有多年未离开这座宅子了,于是他想,他已经变得跟宅子自身一样悲哀了。它那灰色的石墙与暗黑、凝止的湖水间所蕴藏的阴悒业已化作他个人的愁苦心绪。
他还相信他身染怪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亲爱的妹妹病得下十分严重。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德琳,是他家族中另一位仅存于阳世间
的成员,然而似乎每过一天,她就要朝着死神迈近一小步。
“她这一死,”鄂榭闷闷不乐地说道,“就将把我,鄂榭家族的末代孑遗,独自撇在这世界上了。”
他正说着。玛德琳从这长长的房间的远端缓缓走了过去,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便不见了影子。我盯着她,两眼昏昏欲睡,然后心头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惶恐。我再转脸看鄂榭,只见他已用双手掩面,不过我仍能看到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而且他正在无声地哭泣。
玛德琳小姐的病症极为古怪,哪个医生都瞧不出个名堂来。她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单薄,有时候一觉睡去。与其说是睡着了。还不如说是死掉了更形象。多年以来她同病魔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谁知就在我到来的那天夜里,她上了床,并且就此卧床不起。“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活着了,”鄂榭悲哀地摇着头,对我说。
此后的数日内鄂榭和我一直绝口不提他的妹妹。我们花了好多时间一起画画,一起读书。有时他还操起吉他弹上一曲。我尽了极大的努力去帮肋我的朋友,但是却发现悲哀在他心中已如此根深蒂固。那黑*的阴悒笼罩着属于他的世界的每一样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他似乎已接近了疯狂的边缘。
他画了一些古怪的画,唱了一些神秘的歌曲,歌词中尽是些狂野的字眼儿。还有,他脑子里的念头也很古怪。其中有一个想法好像比其他想法对他来说更重要。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万事万物,花草,树木,甚至石头,都是有感知能力的。
“鄂榭府本身,”他对我说道,“就好像是一个活物。当墙壁最初被垒起来的时候,生命便进入了这些石头,此后年复一年,逐渐成长壮大。哪怕是围绕着石墙、聚集在湖面上的空气,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属于这宅子的。你难道没看见吗,”他嚷道,“那石头、那空气是如何塑造了鄂榭家族的众多生灵的?”
这些看法对我来说简直太离奇了,我都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一天傍晚,我正在安安静静地看书,我的朋友非常简短地告诉我,玛德琳小姐已经故去了。他说。他已经决定在宅子下面的一间地窖里停尸两个星期,然后再将其送往最后的长眠之地,理由是他妹妹的病很古怪,医生们还想再研究研究。他请求我帮忙料理一下,我答应了。
我们两个一起抬着盛了尸体的棺材,向下来到房子底部的地窖里。他选定的那间地窖要向下走很长一段才到。但它的正上方恰巧是我的寝室那一带。它从前曾经做过牢房,又小又黑,叫人透不过气来,还装着一扇沉重的铁门。
我们把棺材放下,然后轻轻地掀开棺盖,想最后看一眼死者。我低头朝鄂榭的妹妹脸上望去。这才发现他们兄妹二人是多么相像。然后我的朋友沉着地说了几句话,我终于得知他们二人是同日出生的孪生兄妹,彼此间无须言语交流便能心意相通。
我们对死者不敢久看。她的怪病使得她脸上微微泛出一抹粉红,嘴唇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凝定不变的微笑;这笑容出现在死人脸上,可真叫人毛骨悚然。我们将棺盖重新盖上,仔细钉牢,又锁好了地窖那沉甸甸的屋门,才爬上楼梯,回到阴悒的宅子里。
无比沉痛的几天过去,我发现我的朋友精神错乱的病情有所加重。他不再画画,也不再读书,只是在一个又一个房间里徘徊,脚步迟缓,漫无目的。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光芒已从他眼中消失,一说起话来,他的声音便常常因恐惧而发抖。有时候我想他是企图向我透露什么可怕的秘密,有时候我以为他要发疯了。他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没在看,什么也没在听——听的只是他自己头脑里的声音。我自己开始体会到真正的恐惧了。我感到我的朋友的惶恐,他那致命的阴悒,正在慢慢攫住我的心。
……
